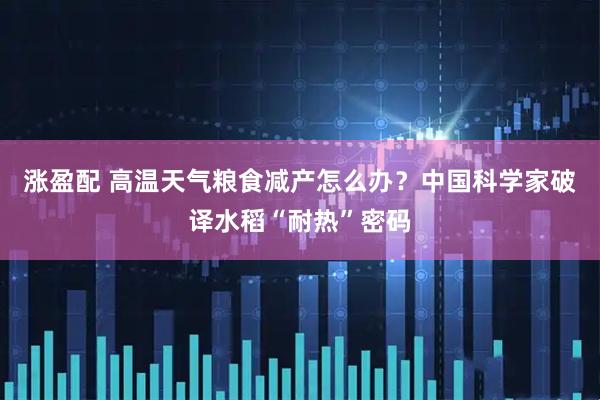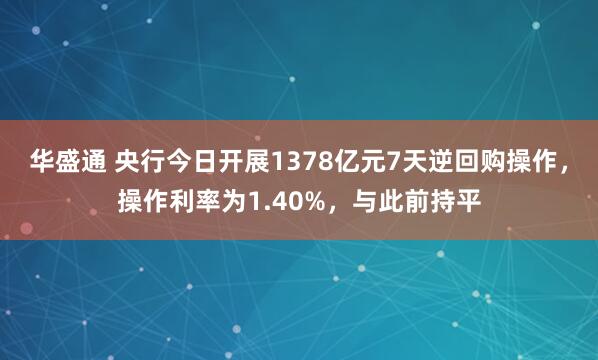1941年底,皖南。 “名单呢?军部已经催了联美配资,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,怎么还没弄好?”曾希圣的声音不高,但屋子里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。

发出这句质问的人,正是新四军第七师的政委,曾希圣。当时的七师,处境相当艰难。皖南事变的硝烟尚未散尽,从重围中九死一生杀出来的将士们,需要重新整编,人心需要稳定,部队需要恢复元气。师长还没到任,整个师的军政重担,几乎全压在曾希圣一个人肩上。说白了,他就是这个新编师的大管家,从粮草弹药到干部任免,事无巨细,都得他来拍板。
很多人可能对曾希圣这个名字感到陌生,但提起他的功绩,那可是如雷贯耳。长征时期,毛主席曾高度评价他领导的军委二局,说“有了二局,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”。这位从事情报工作出身的干将,其行事风格就两个字:精准。他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,尤其是在关乎全局的工作上。也正是这种性格,为后来的一场风波埋下了伏笔。
当时站在曾希圣面前,大气不敢喘一口的,是跟随他多年的秘书王寄松。小伙子很机灵,做事也勤快,跟在曾希圣身边已经好几年了。这次的任务联美配资,就是整理一份全师营以上干部的名册,包括姓名、职务和具体人数,火速上报军部。这任务的背景,是大别山外围的部队刚遭受桂系军队的重创,损失惨重,军部急需掌握干部情况,以便下一步的指挥和补充。
任务层层传达下来,到了王寄松这里,却出了点岔子。向他传达命令的同志一时疏忽,只强调了“曾政委急要”,却漏掉了最关键的一句:“需尽快上报军部”。王寄松不敢怠慢,加班加点把名册整理得清清楚楚,然后一路小跑,亲自送到了曾希圣的案头,想着能让首长省点心。
这下可好,曾希圣拿起名册扫了一眼,脸色“唰”地就沉了下来。他猛地将名册摔在地上,指着王寄松的鼻子就开骂了:“你是吃干饭的?还要我给你代劳吗!”这声怒吼,把王寄松彻底吼懵了。他呆立在原地,脑子里一片空白,完全不明白自己错在了哪里。

曾希圣的火气,源于他对工作的极端负责。在他看来,这份名册是军部要的,政治部整理好后,理应直接呈报军部,怎么能交到他这里来?难道还要他这个政委亲自当通讯员,再跑一趟腿吗?这是工作流程的严重错误,更是责任心不强的表现。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联美配资,这种马虎足以贻误战机,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。
挨了骂的王寄SONG心里那叫一个委屈,他涨红着脸,默默捡起地上的名册,准备退出去。谁知道,曾希圣的火气还没消,竟然追出门来继续训斥。这一下,整个师部机关的人都被惊动了,大家探头探脑,搞得王寄松更是无地自容,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幸好,师部的秘书长及时出来解围。他把王寄松拉到一边,低声把事情的原委掰扯清楚:“小王,别往心里去。是军部要这份材料,传达任务的同志没跟你讲明白,让你受委屈了。”真相大白,王寄松的眼泪差点没掉下来。原来是信息传递出了问题,自己成了替罪羊。
不过,冷静下来后,王寄松也渐渐理解了曾希圣。在那样的战争环境下,一个师的最高指挥官,承受的压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。脾气火爆,或许只是他宣泄压力的一种方式。更重要的是,曾希圣这种雷霆之怒,完全是对事不对人。他苛求的不是下属的态度,而是工作的绝对严谨。

有意思的是,这件事过去没多久,曾希圣又一次问起干部情况。他问王寄松:“大别山的营以上干部,现在到底有多少?”王寄松因为平时工作做得扎实,数据烂熟于心,当即准确无误地报了数。曾希圣听完,还不放心,又转头问了身边几位老同志核对,大家都确认无误。这一次,王寄松不仅没挨骂,还从曾希圣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赞许。
这位脾气像“彭老总第二”的领导,其实内心深处对同志们关怀备至。后来有一次,王寄松因为长期劳累,患上了大叶性肺炎,病情严重,只能离职到老乡家里休养。曾希圣要去军部开会,路过王寄松养病的地方,硬是绕了十里路,骑着一头慢悠悠的小毛驴,专程去看望他。他坐在床边,详细询问了病情,还安慰道:“病是能治好的,你安心养病,身体是革命的本钱,工作上的事不用操心。”一番话,说得王寄松热泪盈眶。
不得不说,曾希圣是一位极其复杂的领导者。建国后,他主政安徽,后来又临危受命,同时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,成为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同时担任两省“一把手”的干部,足见中央对他的信任和对他能力的肯定。他的严苛,他的火爆脾气,都和他搞情报工作时养成的“零差错”习惯,以及战争年代肩负的巨大责任密不可分。
这种看似不近人情的严苛,背后藏着的,恰恰是对革命事业最深沉的责任感。毕竟,在那个年代,一个小数点的错误,都可能意味着血的代价。
淘配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